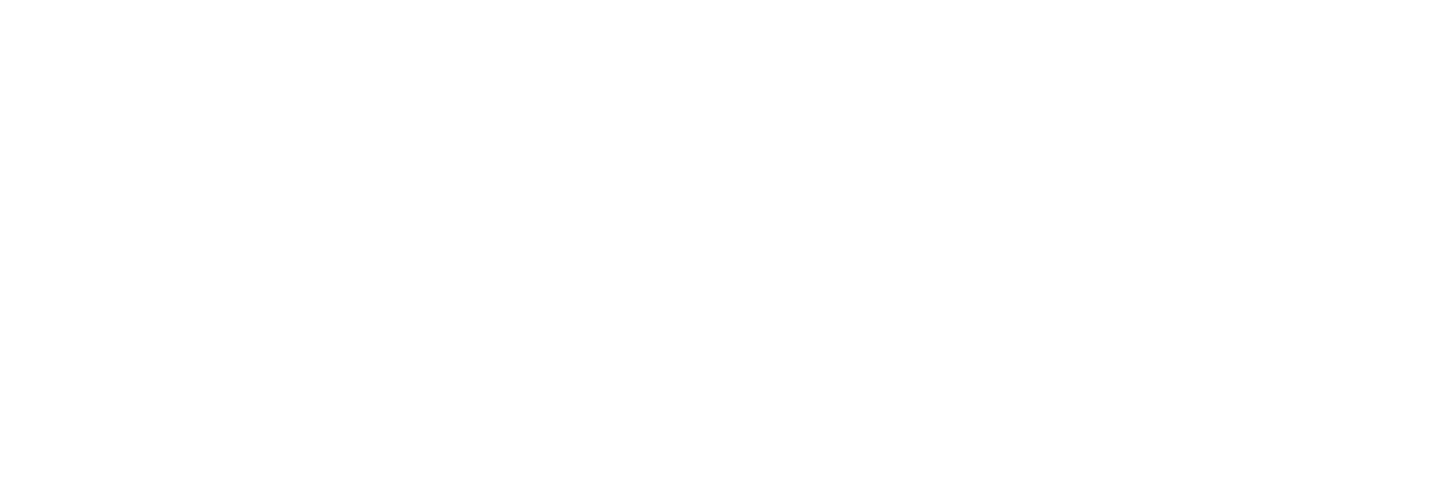相信大家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自古以来,人们对“疾病”似乎早已司空见惯,毕竟长这么大,谁还没生过病呢?
但了解了人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会依从健康建议、做好防护。因为总有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别人才会得病,我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得病?最多偶尔有个小感冒。”尤其是对一些新出现的疾病(如CRIA综合征),或一些看似难以患上的疾病(如皮肤癌),这部分人会因侥幸心理忽视其危害。无论医生叮嘱多少遍,他们都不在意、不依从,最终导致患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不只是个体生命健康受损,还有公共卫生安全的失控,比如刚好这种疾病带有传染性。
应该怎样介绍一种疾病,才能让人们既不恐慌,又引起重视、依从健康建议?这是长久以来困扰医疗大健康与公共卫生领域专家们的一道现实难题。
4年前,这道难题也引发了yl23411永利市场营销学系教授王丽丽的好奇与思考。她找到合作者商议,尝试从行为助推视角以消费者行为学和公共卫生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来解决这一难题。最终,他们找到了一种破题之法,并将研究成果——The effect of disease anthropomorphism on compliance with health recommendations于近日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FT50期刊之一)上。

yl23411永利市场营销学系教授王丽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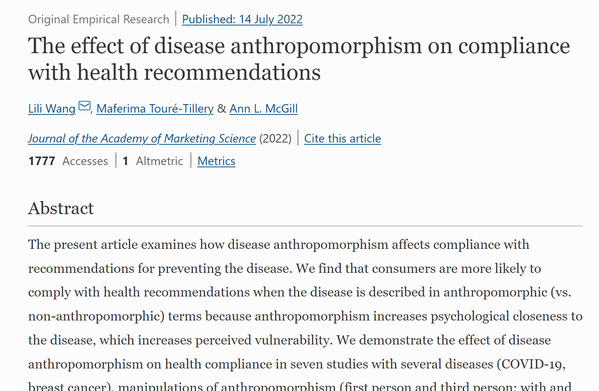
论文于2022年7月14日发表|刊发截图
王丽丽教授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在介绍或宣传某种疾病时,只需要换个介绍或宣传方式,就能让更多的人愿意依从疾病防范及健康建议。这种方式就是,将疾病“拟人化”。该发现将对促进人民生命健康与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产生极大作用。本期专题,我们将为您揭晓王丽丽教授团队这项“商学+大健康”研究的过程、发现及研究的灵感来源。
将疾病“拟人化”,
为何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行为改变?
“你好,我是皮肤癌,我出生在你严重晒伤的皮肤里。尽管我不具有传染性,但我的实力可不容小觑,我有着极强的隐蔽性,会在......”
王丽丽教授团队发现,相比非拟人化的描述,像这样以拟人化的方式介绍疾病,人们更有可能依从健康建议。因为拟人化的描述让疾病从生物病毒“变身”为人类,拉近了疾病与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增加了感知的脆弱性,消除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积极自我偏差(self-positivity bias),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健康依从行为。
“新冠来临时美国很多民众都不愿意依从健康建议戴口罩,因为他们认为新冠只有中国人才会感染。同样,对于皮肤癌,国内很多人也不愿依从健康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皮肤癌是西方的疾病,中国人不会感染。”王丽丽解析道,这实际上是人心理上的“积极自我偏差”在作祟,即“得病的永远是别人”。而我们所做的疾病拟人化研究,让疾病以人的口吻来介绍自己,使得人们不会再因积极自我偏差认为疾病都是别人家的,离自己很遥远。
在得出这一结论前,王丽丽教授团队开展了多个行为实验来探寻疾病拟人化对健康建议依从性的影响。这些实验考虑了不同类型的疾病、不同的拟人化方式,以及不同文化差异,最终得出稳健结论。
“我们2018年开始着手这项研究,基于改变心理距离的四个维度,我们在中国和美国围绕新冠肺炎、黄热病、皮肤癌、乳腺癌,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病做了拟人化实验,包括在美国西北大学校园内的新冠肺炎拟人化海报宣传、与美国当地社区、医院合作进行新冠肺炎拟人化宣传以及在国内做的皮肤癌拟人化宣传实验等。结果发现,疾病拟人化的确能激发人们的健康依从行为,且通过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结果对比验证,我们的结论非常稳健,并不受文化地区差异影响。”王丽丽说。
将疾病“拟人化”并非万能,
不能用时可用数据和图像
在发现疾病拟人化对人们的健康依从行为有作用后,王丽丽教授团队还对这种方法的适用边界做了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这种方法有着显著的边界性,也就是说,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疾病宣传或对所有人群都有用。
“我们发现,将疾病拟人化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描述一些人们不够了解、不确定的新疾病,比如新冠肺炎刚来临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如今就不能再使用这种方法了,因为随着新冠肺炎的持续反复与人们对其日益加深的了解,新冠肺炎与人们的心理距离已经拉近了。”
王丽丽进一步介绍说,这种方法对已患病的人群和一些易感性高的人群也无效,甚至对于已患病的人群来说,这种拟人化的疾病描述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让他想要自暴自弃、不愿接受治疗
同样,对于家族里本就有遗传病基因的易感人群而言,他们周围的亲人中就有人得这种病,使得他们非常了解该病的症状与危害等,因此将疾病“拟人化”对他们也无效。
那么,当疾病“拟人化”这种方法失效时,还有什么办法同样能打破人们心理上的积极自我偏差,让其依从健康建议呢?“数据和图像也能起到一样的作用!”王丽丽表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可视化和患病的概率展示也可能打破人们的积极自我偏差,比如个体饮食习惯、家族病史等因素引发的患病概率;通过图片或漫画让个体感知到自己和疾病的距离等。”
据王丽丽介绍,他们曾在一个皮肤癌的实验中,通过漫画形式改变人与太阳的距离,结果发现会削弱疾病“拟人化”描述的影响,因为通过漫画已经拉进了人们的感知和疾病之间的距离。
研究灵感源于现实“广告”,
营销也能为大健康服务
作为王丽丽教授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一系列发现,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的“有趣结论”,如今王丽丽教授团队正在与相关医院、医疗机构、卫健委等商议成果的应用落地。
他们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真正帮助普通老百姓消除侥幸心理,以免增加患病风险,威胁生命健康。同时也能帮助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等更好地宣传疾病,科学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实际上,王丽丽教授团队的这项研究不仅解决了公共卫生难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还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因为过去的“拟人化”研究对象基本为一些积极正面的事物,比如一些品牌通过拟人化宣传打造品牌的温暖形象。
而王丽丽教授团队的研究创新性地将“拟人化”研究对象聚焦于负面的疾病上,且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研究公共卫生难题破题之法,为“商学+大健康”学科交叉融合做出了初步探索,意义深远。
那么,长期从事消费者行为学研究的王丽丽教授,是如何想到要做这样一项研究的呢?一切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以及一颗想要实现营销公益化的心。
“一开始我是关注到流感的接种率低这一现象,我发现在很多国家,尽管流感的接种率是免费的,但愿意去接种的人很少。于是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依从行为,就像在营销中通过改变消费者的认知,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一样?”王丽丽回忆道,“后来去美国交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一个叫Mucinex的咳嗽药广告,就是病毒以人的口吻在自我介绍。再结合我在网络上看见的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个甲流广告,也是拟人化的描述。当时我就在想,实践中都有这样的疾病拟人化现象了,我们为啥不在理论上研究验证一下呢?如果这种方法好,还能普及到更广的区域。于是我就去找合作者开始了这项研究。”
其实早在莎朗斯通发布“我是中风”健康宣传广告时,王丽丽就开始关注到疾病的拟人化描述这一实践做法。但最终让她决定想要做这项研究的,不只是一次次广告带来的灵感激发,还有内心对“营销也能为大健康服务”的坚信。
“一直以来,大家眼里的市场营销学仿佛只是一门如何赚取消费者手中的钱的学科,但事实上,营销不只是研究如何卖东西,它同样也可以产生公益价值,为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王丽丽说。
附:论文摘要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how disease anthropomorphism affects compliance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ng the disease. We find that consumers are more likely to comply with health recommendations when the disease is described in anthropomorphic (vs. non-anthropomorphic) terms because anthropomorphism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to the disease, which increases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We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disease anthropomorphism on health compliance in seven studies with several diseases (COVID-19, breast cancer), manipulations of anthropomorphism (first person and third person; with and without an image), and participant populations (the US and China). We test the proposed pathwa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and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with sequential mediation analyses and moderation-of-process approaches, and we rule out alternative accounts based on known consequences of anthropomorphism and antecedents of health compliance.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how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negative entities affects consumers’ judgments and behaviors.